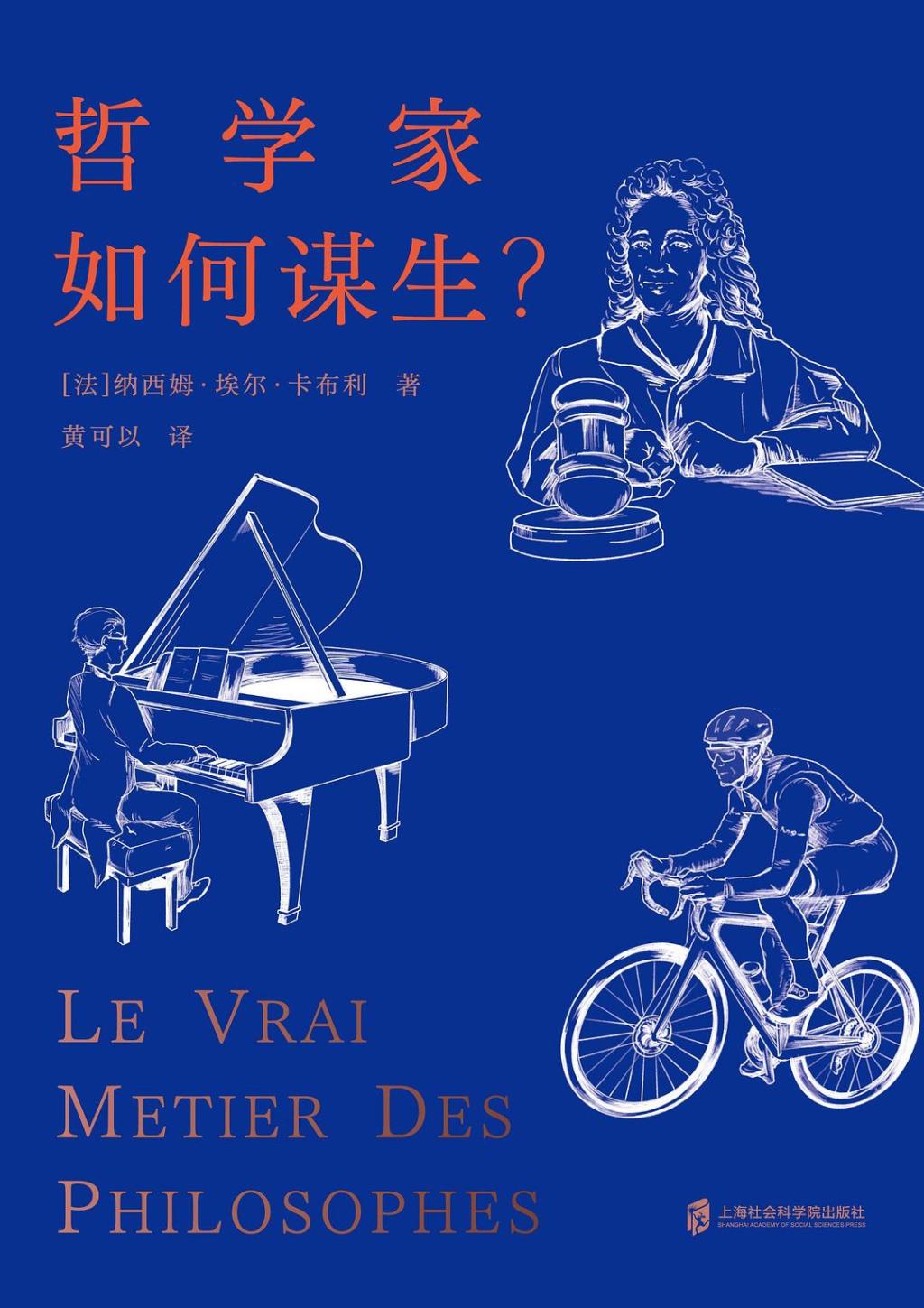
《哲学家如何谋生?》,[法] 埃西姆·埃尔·卡布利著, 黄可以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5年7月版,232页,58.00元
法国学者、电台节目制作人埃西姆·埃尔·卡布利(Nassim El Kabli)的《哲学家如何谋生?》(Le“vrai”métier des philosophes,2024;黄可以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5年7月)出自2023年7、8月间在“法兰西文化”电台播出的“夏日清晨”栏目的四十期节目,是一部面向大众的通俗哲学读物。尽管是通俗读物,作者在每篇文章之后附上的推荐阅读书目既有原始史料,也有研究性的学术著作,为读者进一步思考提供线索。
在眼前我们的生活语境中,这本书尤其是中译本的书名显得很接地气、很应景,虽然与书里讲的内容不是一回事。每年到了高考志愿填报的时候,对考生和家长来说如何选择专业都是一个大问题,在今年变得更加焦虑、纠结。据称目前国内高校本科专业分为十二个学科门类,包括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艺术学,所有学科门类之下的专业共七百零三个。在今年以来有关全球经济、人工智能、职场内卷等舆情波澜的凶猛冲刷下,大学毕业后的谋生问题是专业选择中最大的困惑与焦虑。有人认为今后的就业行情变化太急速了,根本无法预料,因此干脆喜欢什么就选什么吧。话是这么说,最让考生和家长揪心的段子就是赴考场的高考生在电梯里与快递小哥相遇,小哥说他是去年毕业的985大学生。回头再看看本科专业门类,哲学还是排在第一的。虽然这完全与就业无关,但很能引起联想,读哲学的能找到什么工作呢?前天有朋友告诉我,事实上哲学系毕业生不难找工作,最难的是读历史的,让我无语。
哲学家如何谋生?这的确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哲学(philosophy)通常被看作是爱智慧,这是从古希腊就有的定义。正因如此,哲学既是包容广泛的学问同时也是一种值得过的人生——不爱智慧的学问与人生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呢?所谓的哲学家,只不过是比其他人更专注于思考“智慧”与“爱”的概念涵义、思维方式、判断标准等等抽象问题。但是,无论如何爱智慧、爱思考关于智慧的一切,有一个离不开的前提是人首先要活下去,衣食住行不能缺,要赚钱养活自己。通常认为哲学不是一种职业(un métier),不能当饭吃,但是专门研究哲学的哲学家却有可能是一种职业。弗兰西斯·沃尔夫(Francis Wolff)在为该书撰写的“序言”中说,如今的哲学家往往是“哲学老师”,或是大学里的“科研人员”,他们授课、发表论文和著作、组织讲座与研讨会等等。康德是第一位在大学持续授课的哲学家,康德以来的大部分哲学家都是如此。这也是实情。我们更知道在今天还有一些地方的哲学家不但有饭吃,而且吃得还不错——不仅仅是因为在教学岗位上授课和写作,更因为是某种制度之需。除此之外,好像还没听说有职业哲学家这只饭碗,但是这当然不能说体制之外没有真正的哲学家。因此,“哲学家如何谋生”才成为问题,才是讨论“哲学家如何谋生”的真实语境。
通常来说,非职业的哲学家的谋生之道往往在哲学史研究中容易被忽略,或只是作为生平介绍一笔带过。《哲学家如何谋生?》这本书使这个问题凸显出来,其意图和意义并非仅仅是告诉读者那些非职业的哲学家曾经如何谋生,同时也是从“谋生”的视角思考哲学何为,在以“谋生”与“职业”为中心的议题中发现日常生活与爱智慧的真实联系。这还可以从原书名《哲学家的“真正”职业》来思考。正如译者所言,在书名中为“真正”打上引号,大概也是作者在表达对哲学家所谓“本职工作”的双重拷问:对这些哲学家而言,究竟是社会意义、日常意义上的工作才算是“真正”的职业,还是令他们为人所知、跨越时空的哲学思考是“真正”的职业?(205页)
书中介绍了四十位西方哲学家在哲学思考之外所从事过的职业,这些职业听起来很西方也很历史:镜片抛光师、记者、伪币制造者、喜剧演员和脱口秀演员、公共交通承包商、“皇帝的朋友”、机修工、物理学家、市长、高级官员、祭司、艺术经纪人、地理学家、外交家、职业自行车手、邮局职员、图书管理员、作家—作曲—歌手、经合组织经济学家、乐谱抄写员、神父、法官、艺术评论家、皇帝、编辑与斗士、贵族导师、包税人、律师、精神疾病青少年教育家、食利者、抢劫犯、奴隶、人类学家、修道院院长、语文学家、爵士钢琴家、天文学家、历史学家、解剖学家、工人。在这份职业榜单上,有些很出乎意料,如皇帝、“皇帝的朋友”、伪币制造者和抢劫犯;也有些比较特别,如食利者和乐谱抄写员。当然还有一些哲学家如何生存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正如弗兰西斯·沃尔夫在该书“序言”中所说的,在这本书中研究的案例之外,“还存在着一些哲学家,我们不清楚他们靠什么养活自己。他们可能在收租,或者有别人养着。说到底,‘为了生活就得工作,这是社会所必需,也是道德义务’,这样的观点对于古代大部分思想家来说都很陌生,而正是这些‘游手好闲’之辈为我们的文学与科学遗产带来了如此丰富的作品”(序言,4页)。
但是,为了谋生的工作与哲学思考的工作在性质上毕竟大不相同。正如卡布利在“引言”中所讲,一切似乎都在将哲学与工作对立。工作是以智力服务于物质产出或服务产出,目标在于效率和收益;哲学思考在于远离命令、摆脱经济逻辑,完全沉浸于思考与研究。“与工厂的工人不同,哲学家不用打卡,哲学活动也不是朝九晚五。”(引言,2页)因此,卡布利的意图是要探索“这些男性与女性哲学家从事的如此多元的职业与他们的思想有着怎样的联系?哲学家的职业是否只是谋生之道?……还是说,他们从事的哲学与工作之间有着某种类比、因果甚至矛盾的关系?书中的每个例子都具有代表性,而本书的目标在于阐明思想家的‘智力工作’(有点过时的说法)和如此丰富的非哲学工作之间的张力与渗透。因此,关注哲学家智力活动以外的或并行的职业,不仅仅起到丰富人物传记的作用。这些形形色色的职业本身同样有着哲学维度。它们为我们带来启发,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些哲学家的作品。尽管有时以悖论的方式呈现。”说到底,“哲学家的谋生之道,不正是在脚踏实地的同时仰望星空吗?”(引言,3-4页)因此,虽然中译本的书名是“哲学家如何谋生?”,还应该看到作者还有更深的一层意图,就是要研究那些不得不打一份工的哲学家是如何在谋生的工作中思考哲学的。
下面我们就选择书中的几位哲学家,看看他们在谋生的同时是如何思考哲学。
十六世纪法国著名人文主义思想家、《随笔集》(Essais)的作者米歇尔·德·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1533-1592)在他的个人经历中,曾连任两期、前后共四年(1581-1585年)的波尔多市长。他并不愿意出任这份公职,只是因为被市镇官吏投票选出之后被国王任命,无法拒绝。有一个背景作者没有说,那就是蒙田的父亲是一位有贵族头衔的商人,从1544至1556年担任波尔多市长;蒙田自己在1557年后任职于波尔多最高法院,曾两次晋谒巴黎王宫,还陪同过亨利二世国王出外巡视。作者说蒙田在尽心履行市长职责的同时也没有完全沉醉于公共事务,而是给自己保留了一些自由空间,他将这种自由空间称作“店铺后面的小房间”(47页)。哲学家当市长,对履行这份公职的好处是能够以克制、谨慎的态度处理缓和各种冲突。在他的《随笔集》中,蒙田解释说,他永远都与介入公共议题的热情保持距离。这种距离保证了他的判断力,他不会被个人的兴趣蒙蔽了双眼,更不会把个人兴趣包装为公共利益。“在某种意义上,蒙田实现了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描绘的哲学王的理想形象,因为管理城邦的哲学王应当摒除一切对权力的欲望。……但是在柏拉图笔下,哲学王是全知的人物。而蒙田并非如此。蒙田以怀疑论著称,这种怀疑主义在他的思想中和生活方式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49页)在哲学上,蒙田怀疑论的核心议题是怀疑人能够拥有完全把握真理的能力,因此反对任何的独断和自认为绝对正确的自负与固执,从而开创了十六世纪启蒙运动中的批判精神。应该说,蒙田不是为了谋生而当市长,他这个例子讲的是哲学家既然在其位,应如何谋其政。从这个意义上说,“蒙田可能证明了我们不应该忽视这一面:想要更好地对公共利益负责,恰恰应该不要过度关切”(50页)。他的谋生之道是对为官之道的警醒。
与蒙田相似的是古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Marc Aurèle,121-180),当然他的官职更大,他是皇帝,在位时间二十年(161-180年)。卡布利说有许多国王或国家元首都自称为哲学家,但是只有马可·奥勒留既是真正的国家元首,又是完全意义上的哲学家(119页);“当他登基时,已经是斯多葛主义者了,而他的哲学是实行自己的君主职责、使用自己理性和欲望的具体方式。这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行动中的哲学。”(121页)他的《沉思录》(Pensées)是多年来我在“西方经典名著选读”的课程必讲的著作,我总会讲到虽然他的勤奋工作并没有能够挽救古罗马,但是他的《沉思录》却成为西方历史上最为感人的伟大名著。卡布利强调的是,“如果说,所有这些政治和军事职责占据了他人生的大部分,好像没给哲学工作留下什么空间,那我们应该要记得,马可·奥勒留想要的并不是‘从事哲学’,而是‘以哲学家的方式生活’。”(121页)这话说得好,无论哲学家如何谋生,只要有可能,他(她)们总会以哲学家的方式——也就是爱智慧的方式——去生活。这不就是在谋生中思考哲学吗?
十七世纪著名的荷兰哲学家、近代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代表人物巴鲁赫·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1632-1677)曾以磨制玻璃镜片为生,同时进行哲学思考。1673年勃兰登堡选帝侯曾邀请他到海德堡大学担任哲学教授,条件是不可提及宗教,被他婉拒。他打磨的玻璃镜片是用来制造放大镜、显微镜和望远镜的,镜片的打磨抛光是最后一步工序。“这一精细的工作需要相当程度的敏捷、专注与耐心。这些不都正是哲学家必不可少的品质吗?实际上,打磨镜片与撰写《伦理学》(Éthique)这两种活动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2页)“……每一片镜片或每一次论证,都在于看清楚事物原本的真正的样子。……因此,以灵魂之眼看世界,这远远不只是一种隐喻。真理就是一个‘看见’的问题。”(3-4页)说到“看见”,我们都知道斯宾诺莎看见了政府越是打着公共利益的幌子,就越会导致独裁和专制;他还看见了人不是生来就是公民,但必须学会做一个公民。这不是隐喻,是在他的经历中真正看见的。
但是作者忘记谈一个并非不重要的问题;斯宾诺莎于1677年死于肺结核,年仅四十五岁。英年早逝的部分原因与吸入玻璃粉尘有关,这是玻璃镜片磨制工的职业病(参见安东尼·肯尼编《牛津西方哲学史》,韩东晖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5年,191页)。哲学家的谋生之道与职业病的关系似乎也是一种涵义广泛的隐喻,当哲学难以成为一种职业的时候,为了谋生而付出的是时间、精力和生命的耗费。但是话要说回来,既然要谋生,哲学家付出的代价与普通人只能是一样的。
1933年,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逃离德国,先是抵达法国,1941年到了美国,在美国为不同报社工作。“从哲学家到记者,阿伦特的转变根植于她的双重经历:一方面是个人的流亡经历,另一方面则是集体的战争经历。”(7页)卡布利进而指出:“以记者的身份写作与以哲学家的身份写作截然不同。对于一名记者而言,重要的是事实的准确性,以及实时阐明事实的能力;而对哲学家来说,更多是在较长的时间维度上思考,并在这一时间基础上将模糊的事件纳入有意义的阐释之中的能力。”(7-8页)但是,尽管有这种明显区别,阿伦特在从事记者活动的时候仍然将自己的哲学思考运用于对那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悲剧事件的报道之中。“于是,新闻与哲学之间的交汇点便栖身于对事实及对历史事件的关注之中。……对于汉娜·阿伦特而言,记者的训练是一种将自己的思想置于公众讨论视野之中的有效方式。”(9页)
最有代表性的案例是关于纳粹战犯艾希曼的审判报道和论著。1961年4月11日,以色列政府在耶路撒冷开始对纳粹德国军官、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执行“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者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进行审判,艾希曼最终被判处绞刑。阿伦特以《纽约客》特约撰稿人的身份在现场报道了这场审判,并于1963年出版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f the Banality of Evil,Viking Press,1963)这部著作。书中提出的著名术语“平庸的恶”(the banality of evil,准确的翻译应为“恶的平庸性”,在此暂从多年来中译本已流行的习惯译法)以及关于犹太人组织在大屠杀中是否也有责任这两个关键议题引起极大争议。关于“平庸的恶”,批评者们认为这一说法降低了艾希曼罪行的严重性。对此日本青年学者蛭田圭(Kei Hiruta)的看法是比较清晰和公平的,他认为阿伦特的主要意思是指一个人不需要成为一个非常邪恶的人才会犯下非常邪恶的罪行,一个没有深刻动机的平庸之辈(如艾希曼)可能在骇人听闻的罪行中扮演重要角色,只要他没有思考过自己行为的真正意义。同时他也认为阿伦特自己对于引起争议负有部分责任,因为没有阐明这个说法的定义和涵义(蛭田圭《汉娜·阿伦特与以赛亚·伯林:自由、政治与人性》,孟凡礼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24年,66页)。卡布利认为,“无论有着怎样的困难或痛苦的争议,没有人能够否认汉娜·阿伦特在提出假设与寻求讨论中展现出了一种智力层面上真正的勇气”(10页)。
还应该看到的是,作为哲学家和作为记者的阿伦特在此时还有一个重要的交汇背景。此时的汉娜·阿伦特正在重新修订写于1928年的博士论文《爱与圣奥古斯丁》(Der Liebesbegriff bei Augustin),同时经历着对纳粹主义尤其是艾希曼现象的研究和争论。在“平庸的恶”这个概念中所隐含的对物质、权力、虚荣心和道德顺从主义的焦虑,已经出现在对被奥古斯丁所诅咒的“城”的分析之中,使她很自然地把原来就已经认识到的奥古斯丁思想中的贪欲观念、死亡观念和存在主义思想与思考极权政治的邪恶联系起来。以存在哲学思考、质疑、批判人的现实境况和介入政治是阿伦特的重要思想特征,这是我们必须重视从哲学家到记者的阿伦特的早期著作与后期思想的内在联系的重要理由。同时我们也要承认,“哲学家阿伦特研究的案例都较为普遍,而记者阿伦特研究的个案则更为晦涩与复杂”(11页)。
在书中论述的哲学家的谋生工作中,最有吸引力的或许是图书管理员。德国哲学家、数学家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曾经作为图书管理员工作了四十年,负责收拾和整理图书。一方面,“图书馆对他而言是理性的化身,是通过书本的媒介建立人与人之间联系的具体途径”(85页)。另一方面,从“形而上学”这个概念的来源而言,与图书馆也有一种隐秘的联系。“在这一点上,莱布尼茨算是双重的métataphysica学者。说到他的哲学,我们会想到他前定和谐和实体沟通的理论,以及从中提出的关于身心一致的棘手问题。而作为图书管理员的他则关心如何将书籍整理归类到最恰当的位置。”(86页)作为积极的图书管理员和极好的逻辑学家,他发展出了一个目录编纂的系统,以作者名为依据,以主题为补充,这一分类方法在当时是很先进的。最后,卡布利的结论对于喜欢整理藏书的读者来说也是很励志的:“莱布尼茨的哲学让我们了解到他是一个关系的思想者,而因为图书馆管理员的工作,他又是关系的实践人。……在图书馆里整理书籍,对于一个关系(vinculum)理论家而言,不正是一种在人与人、年代与年代之间创建牢固关系的方式吗?”(88页)
至此,读者也都看得很清楚,卡布利在书中探讨了各种职业对哲学家继续从事哲学思考的影响。也就是说,那些看起来只是谋生之道的工作并非只有赚钱糊口的意义,而是与哲学思考之间存在着微妙而真实的联系。“或许,哲学家在哲学思考之外所从事的‘真正’工作,才是他们训练思想的‘秘密实验室’”(见该书封底语)。这是对于原书名《哲学家的“真正”职业》的一种有意义的阐释。
受到这本书的启发,我们还可以把“哲学家”与“谋生”这两个概念投射到十八世纪法国的一条比较模糊和更加敏感的地带,由此而发现一种或许更为激动人心的与思想捆绑在一起的谋生之道。著名的欧洲文化史专家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在他的《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The Literary Underground of the Old Regime,1985;刘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中通过大量档案材料,揭示了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前的一个隐秘的思想启蒙世界。
正是在这个世界中,我们可以发现有一群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称作哲学家或类似哲学家的人是如何谋生的。他们可能是盗版书贩、受雇佣的文人写手、来来往往于边界的走私小贩甚至可以成为警察的线人,这些活动既是他们的谋生手段,同时也是他们探索思想、传播思想的渠道,也是窥测政治风云的精神网络。兼文人、书商与密探于一身的布里索就是这么一个极其真实、复杂的人:“当布里索发现他的道路遇阻,他不得不与体制妥协。当体制监禁了他,没收了他的作品,他与其警方达成谅解。当它没能使他作为一名哲学家谋生时,他成为一个雇佣小册子作者和‘苍蝇’。当大革命来临时,他投身于革命,不是作为回忆录中所写的无私的理想主义者,而是作为旧体制的失败者决定在新体制里救赎自己。”而在格拉布街,“像布里索这样的人炮制报纸和小册子、海报和漫画、歌曲、谣言及毁谤作品,所有这些将个人争吵和派系斗争转变成了关乎法兰西命运的意识形态斗争”(《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71页)。该书第三章“逃亡中的小册子作者”所研究的勒塞纳,就是伏尔泰所描写的“可怜鬼”的典型:“他们挣扎着维持其悲惨的生活,打着落到眼前的无论什么样的零工——编选集,给杂志写稿,推销手稿,走私禁书,给警方做密探。”(106页)这些谋生手段放在今天其实也并不陌生,这种“可怜鬼”也可以看作是流亡中的哲学家或文学家。这些来自外省的文学青年、从主流文学大家中被淘汰出局的文学无产者、半饥半饱的雇佣文人、投机的盗版书商、警方的线人、文字皮条客、性丑闻的编造者和传播者在各自的精神领域中未必是干哲学家的活,但是他们之所思所言总是带有反体制、反权力压迫的叛逆性,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哲学”不在于如何解释世界,而是在于改变世界。那么,他们的谋生之道不是比卡布利所讲的那些正牌哲学家的谋生职业更具有哲学的使命吗?
最后还应该看到的是,在哲学家、文学家以及各种专业的知识分子的谋生之道中,还有一些经历是很悲惨的。二十世纪俄罗斯著名女诗人、散文家、文学翻译家玛丽娜·茨维塔耶娃 (Марина Ивановна Цветаева,1892-1941)的一生(1892-1941)既是艰难的、悲惨的,也是高傲的、充满生命激情的。她在1922年离开苏联,先后在柏林和巴黎生活了十几年,最后在1939年回到苏联。事前茨维塔耶娃也知道回去是一条艰难的路,但没有想到要承受那么深重的痛苦。回国两个月后,女儿阿莉娅在8月27日深夜突然被捕;10月10日,身患重病的丈夫谢尔盖也被逮捕。接下来的日子就是为了得到女儿、丈夫的消息而到处奔走,为了自己与儿子的生活而苦苦挣扎。1941年8月她带着儿子穆尔被疏散到鞑靼自治共和国境内的小城叶拉布加,为了谋生前往莫斯科作家协会所在地奇斯托波尔,请求迁居该处并在作协基金会即将开设的食堂谋取一份洗碗工的工作。但是她这一谋职请求被作协领导拒绝了,这是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她于8月31日趁房东外出时悬梁自尽。在茨维塔耶娃死后的一个半月,她丈夫谢尔盖·埃夫龙被处决。1945年帕斯捷尔纳克在与以塞亚·伯林(Berin,I.)的会谈中提起1941年茨维塔耶娃自杀时的处境,他认为如果不是那些文学官僚对她如此绝情,简直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这种事情或许也不会发生(以塞亚·伯林《苏联的心灵》,哈代编;潘永强、刘北成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63页)。帕斯捷尔纳克说的“绝情”当然就是指作协拒绝给她一份得以谋生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在当时的苏联体制中,以她的身份根本无法在体制之外找到工作。
“是时候摘下琥珀,/ 是时候更换词典,/ 是时候把门上的灯 / 熄灭……。”(《致一百年以后的你:茨维塔耶娃诗选》,苏杭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442页)当茨维塔耶娃感到自己的生命必将被内外的黑暗所吞噬而写下这些诗句的时候,或许她还曾经想到了希望获得但终被拒绝的那份工作。一个为痛苦讴歌的女诗人,这是茨维塔耶娃留在永恒的诗歌天幕上的高傲的形象。


